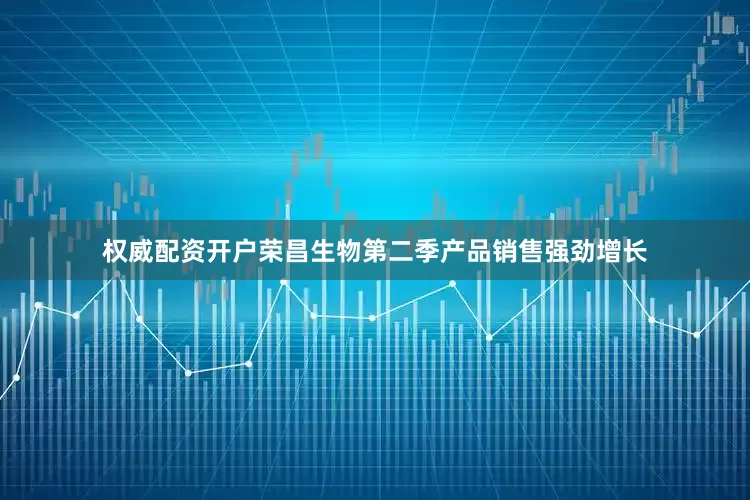自1938年至1940年,我有幸在中共中央东南局任职。在那段时光里,我在皖南溪县的丁家山村与叶挺、项英、曾山等同志并肩工作、共同生活。期间,我有幸聆听项英同志讲述关于江青的一些过往故事。
1955年,一场震动全国的“潘汉年、扬帆”事件爆发,尽管众人对此缄口不言,然而那些洞悉内幕的人却心照不宣,彼此心知肚明,对江青的狡黠与残忍有着深刻的认知。

顾梦鹤、王莹以及蓝苹(即江青)。
“婚姻的选择本就多样,却为何非得选择与这样的人结为连理?”
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与深切敬仰,项英同志向掌握江青在上海期间详情的军部扬帆同志展开了调查,并依据扬帆同志所撰写的证明材料,向延安的党中央发送了一封加密电报。
此份由项英签署的电报,针对“蓝苹”在三十年代的种种不良行径,直言不讳地揭示了:
此人不配与毛主席结婚。
处理此电报的,是新四军司令部的秘书长李一氓同志。
遗憾的是,传言毛主席本人并未收到那份电报,却不幸落入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之手。康生竟胆敢私自扣留此电报,并误导中央称江青的历史纯洁无瑕。更有甚者,他事后向江青透露此事,致使江青对项英、扬帆和李一氓同志始终怀恨在心。

扬帆
自上海解放以来,扬帆同志担任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职,后晋升为局长。然而,1955年,他与潘汉年一同被捕,随后被以“潘、扬反革命集团”的罪名判处刑罚。
在漫长的二十余载牢狱生涯中,扬帆饱受折磨,双目几近失明,晚年更是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。
关于潘、扬冤案的真相与谬误,此处不予赘述。早在1983年8月23日,中共中央便颁布了通知,对他们予以昭雪平反,并恢复其名誉。
其遭受责难的关键因素之一,便在于他所揭发的江青之行。
1978年十月,扬帆同志的伴侣李琼女士前往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身处“劳改”中的扬帆。途经武汉之际,她特地给我寄来了一封详尽的信件。
身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,我正身处京城参加重要会议。接到消息后,我即刻着手搜寻扬帆同志的下落,并迅速将他接到武汉一家顶尖医院接受治疗。
1979年1月8日,我特意调配了一架安—24型专机,将扬帆安全送返上海,以便其接受治疗。

陈丕显
1952年三月,我自苏南区党委书记一职调任至上海市委,担任代理第一书记。鉴于上海对江青的过往了解颇深,有关她个人生活的种种传闻亦不绝于耳。因此,我对她的态度是保持距离,内心有所保留,但表面上依旧保持着礼貌。“不看僧面看佛面”,毕竟她的身份颇为特殊。
幸而江青抵达上海后,便迅速联络了柯庆施与张春桥。直至柯庆施不幸病逝,江青才与我交往频繁。记得在1965年某日,江青特地邀请我与谢志成及张春桥一同前往西郊宾馆,她所居住的地方共进晚餐,此举当是对于我们支持她推进革命现代戏的答谢。
席间闲聊,江青问:
阿丕,学历是?
自13岁投身革命事业,在此之前,我仅是间断性地接受了七年的教育。面对她的提问,我如此回应。
“我只上过小学。”
江青自述:“我的学历仅到小学。”接着,她转向张春桥询问,“春桥,你的情况如何?”
“我是中学毕业。”
“小谢呢?”
“我读的是中专,中学也算。”
“我与丕显均仅受过小学教育。”江青随后若有所思地补充道,“有时,书籍读得过多,未必就能真正派上用场。”
江青神态悠然,流露出一抹得意之色,言谈间不时透露出对知识分子的轻蔑,同时也不自觉地慰藉着自身文化水平的不足。

也是酒后言辞略显放纵,在宴席上,我们不禁回忆起投身革命的过往。我提及,谢志成参与革命活动,深受华家的深刻影响。
“华家?”江青随口问。
谢志成回答说:
在我故乡无锡求学期间,我结识了一位极为要好的同班同学,她名叫华辉,亦被称为华英。华辉的家人思想开明,早年便投身并坚定地支持革命事业。她的哥哥华斌与姐姐华萼均是在青年时期便加入了党组织。他们时常向我们二人传扬革命思想,激发我们投身革命的决心。
1934年,华辉赴上海参与“反帝大同盟”的活动。返抵无锡后,她慷慨地将一条衬裙赠予我,称这是与她保持组织联系的同志所赠。而这件衬裙,原来是上海的蓝苹转赠给那位同志的。
华辉赠予我的衬裙,实则寓意着一种“牵挂之物”,她期望我能够早日融入革命队伍。

陈谢夫妇
江青闻言,脸色骤变,急忙道:
“绝无此事!绝无此事!你难道不知道我那时的名字吗?”
“蓝苹啊,我倒是听闻了你出演的《大雷雨》。”志成直言不讳地说道。
“同学叫啥?”
“她以华英为名,在华家排行最小,遗憾的是,她在福建英勇就义。她的姐姐华萼,曾与您共度牢狱之苦。此外,我还听闻,有一位名叫陶方谷,亦名陶永的志士,也曾与您并肩在囚笼中度过艰难时光……”
在担任新四军军部速记员期间,志成曾为叶挺、项英、曾山等领导人担任速记工作。他记忆力非凡,对于那段亲身经历的往事,记忆依旧清晰如昨,言谈间不经意间便脱口而出。却未曾料想,这番话语竟触及了江青心中的隐痛与敏感之处。
“绝无此事!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!我从未被捕,也从未将任何衬裙赠予他人……”江青的声音陡然变得尖锐,语气中充满了坚定。
气氛瞬间变得极其尴尬,张春桥只是埋头用餐,连头也未抬,默默无言。
然而,江青随后却坦诚,在上海期间曾遭敌人拘捕,但她坚称并未泄露身份,亦无“自首”、“动摇”之行。她解释道:“我是在假哭之后被释放的。”
原本,并未料及需揭开江青的过往真相,不过是随口提及旧事。反倒是江青自身,因心虚而显得格外敏感。
后来才知晓,江青对她1934年在上海遭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拘捕的往事始终缄口不言,这成为她心头难以抚平的痛楚。1964年,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透露,江青曾向他询问,她在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曾被巡捕房“扣留”的情况,并询问公安局是否存有她被扣留时的指纹档案(即她自首时的手续记录)。
实际是黄要找后送她。

在那次对话结束后,江青在杭州暂歇期间亦向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提及,她自上海以来未曾遭遇过被捕的经历。
与此同时,她亦要求上海市警卫处处长济普前往市局档案处,查阅她被捕的相关档案资料。
不久之后,江青再次向王芳进行说明,指出她要求王济调查敌伪档案,实际上是为了查找浙江某位不良分子,因此需要查阅该份档案。
江青旨在销毁罪证。
然而,在1968年2月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,她竟然倒戈相向,无中生有地指责上海公检法的同志对她进行了所谓的“黑材料”陷害。她借助空军吴法宪的力量,将上海市委负责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、公安局长黄赤波、警卫处长王济普等二十余人分批押解至北京,并投入监狱。此外,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、吕剑光等亦遭受牵连。

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彩的历史,在“文革”中备受迫害。大哥华渭臣、二哥华斌、姐姐华萼、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、被斗、被关,受尽凌辱和折磨。华萼被迫害致死。
此事件于我二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,并刻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。
江青在“文革”中整了无数的人,其中不少是知其劣迹的人。我想,后来江青、张春桥一伙对我残酷迫害,非要把我打成“叛徒、特务、老反革命”,置于死地,大概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长胜证券-深圳股票配资论坛-全国前三配资公司-在线配资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